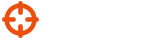金发碧眼的美国工程师杰克摊开双手:抱歉,我们已经尽力了。这台机器的核心部件可能存在不可逆的损伤,建议您考虑更换新设备。
就在这时,一个穿着洗得发白工装的中年人走进了车间。他个子不高,脸上布满岁月的痕迹,双手粗糙却稳健。

这家年产值过十亿的大型制造企业,主营精密零部件加工,客户遍布全球。他们的产品小到手机零件,大到航空配件,精度要求极高,容不得半点差错。
早上七点半,当第一批工人走进三号车间时,发现那台德国进口的五轴联动数控加工中心停在那里,操作面板上的红灯不停闪烁。
操作工王师傅满头大汗:不知道啊,昨天下班前还好好的,今天一开机就这样了。
陈海立即上前查看,按了几个按钮,机器毫无反应。他打开电气柜,里面的线路看起来都很正常,没有烧焦的痕迹,也没有松动的接口。
半小时后,技术部的工程师们围在机器前,各种仪器轮番上阵。测电压、查程序、检油路,忙活了一上午,还是找不出问题所在。
这台机器是2015年从德国进口的,当时花了800万人民币,是整个车间的核心设备。它负责加工最精密的零件,精度可以达到0.001毫米,相当于头发丝的百分之一。
赵建国的脸色变了。他很清楚,一旦涉及到原厂维修,不仅费用高昂,时间更是没谱。
邮件很简短:根据描述,可能是主控板故障,建议更换。如需技术支持,可安排工程师前往,费用另计。
光一块主控板就要120万,还不包括人工费和差旅费。如果德国工程师来,每天的费用是5000欧元,至少要待一周。
我们可以试试找美国的技术团队,他们在亚洲有分公司,可能会便宜一些。李明建议。
领队的叫杰克·威尔逊,四十多岁,斯坦福大学机械工程博士,在数控机床领域有二十年的经验。他带来的两个助手,一个是电气工程师,一个是软件工程师。

杰克很有信心:放心,我们处理过很多类似的案例。给我们一周时间,应该能搞定。
美国团队的工作方式很专业。他们先是花了两天时间做全面检测,用各种先进的仪器测量每一个参数,记录每一个数据。
控制系统正常,电气系统正常,液压系统正常......杰克看着检测报告,眉头越皱越紧。
第二周,美国团队改变了策略。他们开始更换零部件,先是换了几个传感器,机器还是不动。又换了伺服驱动器,依然没用。
那些等着零件的客户开始催促,有的甚至威胁要取消订单。财务部算了一笔账,每天的直接损失就有四十万,如果算上违约金和客户流失,损失更是无法估量。
杰克显得很疲惫:赵先生,我必须实话实说。这台机器的问题很罕见,我们用了所有的检测手段,更换了能换的零部件,但就是找不到根本原因。
赵建国闭上眼睛,深深吸了口气。1200万,外加六个月的等待,这对公司来说几乎是致命的打击。
他想不通,一台好好的机器,怎么突然就坏了?而且坏得这么彻底,连美国专家都束手无策。
其实,赵建国心里也没抱太大希望。这些年,公司的设备越来越先进,越来越依赖进口。每次出问题,第一反应就是找外国专家。国内的技术人员,似乎总是差那么一点。
八级钳工,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。当时,技术工人分为八个等级,八级是最高级别,相当于工程师的待遇。能评上八级的,都是技术顶尖的老师傅。
这个我也不确定,但是听说他什么机器都能修。前几年,南方一家工厂的进口设备坏了,就是他修好的。
他已经退休了,不用手机,家里只有座机。小刘通过东方重机的老同事,辗转找到了他的电话。
数控的啊......李玉成的语气有些犹豫,我这把年纪了,数控的东西不太懂。
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装,拎着一个老式的工具包,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退休工人。

他没有打开任何仪器,也没有查看任何数据,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,观察着这台庞大的机器。
他开始绕着机器走,走得很慢,每走几步就停下来,有时候伸手摸摸机身,有时候趴下来看看底部。
杰克在一旁看着,忍不住对助手说:他在干什么?不看数据,不用仪器,光凭眼睛能看出什么?

不行!杰克激动起来,这个位置是传动系统的核心部位,随便拆卸会影响精度的!
在放大镜下,那个轴承座看起来确实有些异常,表面不太光滑,似乎有轻微的磨损痕迹。

你们测的是整体尺寸,但这个形变很特别。李玉成解释道,它不是均匀的形变,而是局部的微小扭曲,可能只有0.02毫米,甚至更小。
0.02毫米?杰克瞪大了眼睛,这么小的形变,怎么可能影响整台机器的运转?
李玉成站起身,指着传动系统说:这个位置是整个传动链的关键节点。别看形变很小,但它会导致传动轴在高速运转时产生微小的偏心。这个偏心会被逐级放大,最终导致整个系统失去精度。
控制系统检测到精度偏差超过阈值,就会自动停机保护。他继续说,所以机器能启动,但主轴不转。
做了四十多年钳工,摸过的机器比你见过的都多。李玉成说,每台机器运转时都有自己的震动频率,正常的震动是均匀的,有问题的震动会有细微的异常。
刚才我让机器开机,就是为了感受它的震动。他解释道,在这个位置,我感觉到了不正常的震颤,很微弱,但确实存在。
作为一个博士,一个在这个领域工作了二十年的专家,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经验。
不是书本上的知识,不是仪器里的数据,而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,融入骨血的经验。
里面的工具很简单,甚至可以说简陋。几把锉刀,几个小锤子,一些垫片,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小工具。
先是用千分尺仔细测量轴承座的各个位置,然后在一张纸上画着什么,似乎在计算。
他要把垫片放在准确的位置,然后通过调整周围的紧固螺丝,让轴承座恢复到正确的形状。

李玉成继续说道:这种形变,不是自然磨损造成的。它的位置太特殊了,形变的方式也很奇怪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......